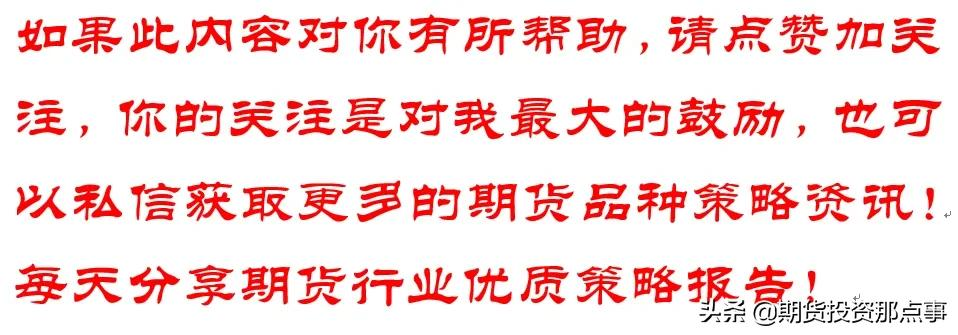002283股票质押率是多少:“中华的位置”与“世界秩序”:以历史角度看金融问题
最近,随着上证指数重新回到3000点附近,微博上有一张14年前上证报《多方绝地反击,3000点先是后得》的截图火了。
这则报道发布于2008年4月23日,当时上证指数在127个交易日内自6000多点暴跌至2990多点。没想到14年一个轮回,我们又要进行一轮3000点攻防战。
人们都说历史是在不断演进的。对于经济周期、金融周期、投资周期,有投资者认为历史可以重演,但也有投资者坚信此时此刻并不同于彼时彼刻。
资本市场如此的历史周期变化,令我们不断思考如何用“历史学”眼光去看待金融问题。这便是本文想要探讨的一个命题。
一个简单的“历史角度研究金融问题”的案例是:历史上,一个国家国民储蓄、整体债务、储备货币三个参数的多寡能够决定其抵御经济危机和信贷崩溃的能力。类似的选题或者研究角度还可以很多。
太多了,那只能从核心思考者角度出发研究。我们认为当今世上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两位思考者是易中天先生和瑞·达利欧先生。
本文的标题分别取自易中天先生的《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以及瑞·达利欧先生的《原则 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但本文最终目的可能也只是提供一个契机,让读者找到继续思考下去的一条线索。
对于两位的介绍应该不需要我们再赘述,期待能从这两本著作中解析出两位思考者的一些逻辑来回答上述命题。
易中天、达利欧对历史周期的思考
黄炎培教授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周期律”,总结出中国历史上的兴衰交替,每个朝代从兴起到顶峰再到衰落,循环往复,连绵数千年而不断。
黄教授同时把这个历史周期律拓展至更细分的层面,提出:“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
可见“历史周期律”拥有普遍适用性特点。但历史周期律能否被用来解释所有的问题呢?其实也未必。
历史周期律甚至不能单独解释所有历史问题。
对于外来文明冲击和中国历史周期律的关系问题,著名历史学者易中天教授曾有过这样的论述:“首先历史不可假设,要假设的话,我们必须这么假设:如果西方没有发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及大航海,就没有后来的鸦片战争。我前面已经说过,清代已经把中华帝国制度除了腐败以外的其他问题都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样?我的猜测可能是由腐败而腐烂,由腐烂而腐朽。将来历史是怎么样?不知道。”
易中天对历史周期中每个阶段的点评是不同的。比如,他在接受燕京书评采访时说过:“到了唐代,是唐文明、阿拉伯文明、拜占庭文明三足鼎立,我在《易中天中华史:禅宗兴起》实际上是说这一点。反倒宋是一枝独秀——到了宋代的时候,全世界只有宋是唯一兴盛的文明。元明清完全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才有那种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华’这个说法——虽然这个说法我也不同意,但崖山以后走了下坡路。”
无巧不成书,在世界投资界中鼎鼎大名的瑞·达利欧就是一个明确的“历史周期”信仰者和实践者。
他认为,通过对1500年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帝国的历史周期研究,当前的中国符合他所认定的一个国家崛起的所有条件。中国有 “足够有能力的领导 ”来增加国家的财富和力量;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教育系统,民众具备强烈的工作热情,并且向 “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开放。
这位世界最大对冲基金桥水的实际掌控者最新出版了一本名为《原则 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的新书。书中他试图厘清世界历史上老牌帝国兴衰的过程,并提出了“3大周期、8个决定因素”等新颖的历史方法论。
达利欧先生在书中还写道:“繁荣与萧条、和平与战争的历史阶段,就像潮水那般来了又走。”
我们不禁想象,在他对历史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周期”的信念中,是否藏有有某种宿命论?
从上述两位思考者的文字中获得灵感,我们能否也可以畅想一下在包含投资在内的金融领域以“历史视野”来做研究和决策呢?又或者,我们能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历史视野可能无法被证明能帮助我们解决某些特定金融问题?
要完成对以上这些问题的解答,可能需要长年累月的研究积累,势必需要“读万卷书”,可能还要再加上“行万里路”。
我们不敢说已经读懂了易中天先生的《易中天中华史》系列以及瑞·达利欧先生的《原则 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更遑论能有如此深厚的学术沉淀去解答历史学和金融决策的关系问题。
但通过阅读两位的著作,我们发现以历史角度看宏观问题是达利欧最典型的标签之一;而以历史来论中华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则是易中天先生最鲜明的观点之一。
从这条出发,我们力图从两位思考者的著作中找到一些灵感,为读者带来一丝启发。
瑞·达利欧眼中的中国历史
瑞·达利欧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的对冲基金经理,对中国有着客观而深入的研究。
在《原则 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中,达利欧在其第六章《中国大周期及其货币》(The Big Cycle of China and Its Currency)用心发挥,将他的观察与思考详尽记叙约2万字。
在这一章的开始,他便坦言关于中国的研究,他选择坦诚表达自己的观点。一方面他认为不诚实将让自己的尊严受损;另一方面,他已经做了近36年的研究,有向世界分享自己最新成果的动力。
章节中,他探讨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思想文化的诞生,并且回顾中国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衰落历程,以及审视起于微小却逐渐成长为世界强国的兴起。
下图是达利欧绘制的世界各大国在1500年至今的相对国力估测排名。能看得出来中国在1500年以前是领先于其他国家的,虽然经历了下跌,但是在2000年以后国力急速上升,如今已经有着赶上美国的势头。
图源:达利欧的领英
这个目的是为了解释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他认为,理解中国的第一步就是要对中国约4000年的历史有个基本的了解。因此他简单回顾了公元600年之后的中国历史,为此绘制了一张自公元500年至2000年的一张相对国力排名图。和上面的图表非常相近,不同的是时间周期更为久远,且仅标注了中国一个国家。
图源:达利欧的领英
而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都可以被看为是一种反常现象,不是常态。因此这段200多年的历史教训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他尤其关注中国1800年后迅速下滑以及1950年之后重新崛起的两个节点。他认为,从1800年左右起,亚洲的财富和权力逐步转移到了欧洲,这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一次的财富和权力转移,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中国的衰弱。
除此以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周期一般是300年左右,而每个朝代都会吸取上个朝代的历史经验教训,从而开启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的伟大思想者也非常热衷于学习历史,进而帮助他们计划和决策。由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以及中国人对历史的深入研究,相比美国人更愿意寻求快速成功,中国人更感兴趣长期发展战略。
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是建立在长久的历史智慧的积累之上的。
中国的主要思想智慧令中国人有着和美国人不一样的行为方式。由于独特地理位置的存在,在中国千年的历史里,战争多发于境内,中国境外的却并没有很多,即使有境外的战争,主要也是为了树立对内的实力,以及维护安全和贸易,而不是为了占领。
由于金属货币(比如银元、铜币、金币等)的实际价值非常高,使得中国各朝代都能够较好地控制通货膨胀。
正由于中国内在大循环的存在,中国自己的货币体系也是非常独特的。达利欧表示自己所观测到的两次恶性通胀都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内战的存在,货币出现了极端的贬值。随后1948年,人民币作为法定货币发行并保持有限供应终结了恶性通胀。第二轮通胀则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
图源:达利欧的领英
历史周期波动下的桥水
其实桥水基金在成立的47年中也屡屡遇到过很大的风险。最近的一次则是2020年第一季度美股连续熔断的历史性时刻。当时有传闻称桥水基金将会“爆仓”,其中桥水基金的旗舰产品纯阿尔法基金产生了20%的回撤,并且有传闻称LP沙特基金正在考虑撤资。
然而达利欧却从历史角度出发,把握住了未来的趋势方向。
当时很多人就分析过桥水会不会因为这一事件就此陨落。他所采取的方法很简单:主动发声,呼吁所有人保持耐心,并表示桥水基金非常安全,所有的一切都在预期之内。
不仅仅是通过英文的渠道,达利欧甚至发了一条微博,为自己代言道:桥水的财务状况非常稳定,既没有出现在目前情况下与我们预期不符的投资亏损,也没有出现与我们过去45年来做投资的常态不符的损失。
图源:微博
达利欧能够准确把握历史周期,并且预测政府决策,这也是他能够持续获取超额收益的秘诀。
后面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了,美股随后迅速反弹,并且走出困境,指数一路上扬。桥水基金的规模也进一步增长。截止至2021年年末,桥水基金依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
尾声:历史与文明——易中天遥望达利欧
人们之所以“通常会错过生活中的重大历史演变时刻,是因为他们只经历了正在发生的微小的事情。”当大多数投资者“像蚂蚁一样”对世界采取碎屑隔绝的看法时,瑞·达利欧坚信他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
在达利欧先生看来,如果一个人没有看到历史演进下的世界秩序大势,就看不见历史周期循环。
他写道:“我认识的投资者和高层经济政策制定者中,几乎没有人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和原因有任何出色的理解。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是最顶尖的人物。”
书中他将人类几个世纪的历史以“创造-财富”的维度展现。
尽管瑞·达利欧没有明确表示他不同于这些人,也没有明确表示过自己拥有这种“基于历史层面的理解能力”,但很少有读者会怀疑他对拥有这个能力的自信。
“三大文明(指中华、伊斯兰和西方现代)的次第辉煌,不过是‘文明结构’的层层展示和打开。而这其实就是历史本身。”
这和易中天先生的文明兴衰观点有相符的地方。在《易中天中华史》这套书中,他努力构建起文明和历史的关系,并且认为:“文明的秘密,在意志,也在结构。文明是有结构的。任何一种文明,都由三部分组成:方式、精神和价值。价值外化,就表现为精神。精神落实,就表现为方式。方式其表,精神居中,价值是内核,是为‘文明三要素’。”他在总序言中写道:
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经历了由兴盛转向衰落的时期,这个过程无法不和每个文明的初生、辉煌、落寞相联结。
瑞·达利欧也有自己的文明观,但他的表述方式非常具有“统计性”。他在新书中展示过去500年里11个主要国家的相对财富和权力地位变化趋势,每一项财富和权力指标都是由8个不同的决定因素组成,分别为 (1)教育,(2)竞争力,(3)创新和技术,(4)经济产出,(5)世界贸易份额,(6)军事实力,(7)金融中心实力,(8)储备货币地位。
也因此,我们民族必将被赋予新的使命,再次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至于赋予者是谁,并不重要。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管他叫‘历史’。这不是想当然。
作为对照,易中天先生认为“只有中华、伊斯兰和西方现代,才代表了三代文明、三种类型、三个时代和文明三要素,同时最具世界性。因此,这三大文明有可能就是文明意志的集中体现,当之无愧地可以成为‘第一世界’。”
对于历史周期的解释,相对达利欧专注于分解财富和权力的8个“统计性”决定因素,易教授更倾向用“文学性”的笔墨来诠释。
下坡路上,没人刹得住车。当然,这下坡路缓慢地走了一千多年,其间既有一蹶不振,也有路转峰回。”
比如,关于中华的历史兴衰周期,他曾用绚丽的笔锋写道:“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 以及四年后的安史之乱,也许是一个分界点。大唐帝国对外败于阿拉伯,对内亡于藩镇割据,中华文明投向外部世界的目光从此收了回来。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开阔,全都变成了明日黄花。时代风气由宋的纤细,元的空灵,直至明的世俗,清的官腔。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魏晋六朝的思想解放,自然也风光不再。明末清初后,鸦片战争前,中华再无思想家,对人类文明也再无像样的贡献。人们津津乐道自我陶醉的,是核舟记、病梅馆、鼻烟壶,以及三寸金莲。只有《红楼梦》和纳兰词,敏感地唱出了末世的挽歌。那是一 种‘睡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的无奈。
当然过程中,还需受国家债务水平、贫富差距等问题的主导,但经济历史循环往复的走向是不可逆转的,即使可以慢一点。
对于此,达利欧也有同样的观点,他得出了世界经济从重建到繁荣,从繁荣到泡沫,又从泡沫到毁灭,最后从毁灭到重建的历史定律。
两位思考者类似本文中这些具有关联性、相似性的思想光芒还有很多,我们要细细品读,即使作为读者,我们自然可以对“统计性”或者“文学性”文笔有偏好。
身处地球两端、专业上毫无任何交集、背景极为不同的两位思考者,却分别用“统计性”和“文学性”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为世界谱写出相得益彰的历史周期乐谱。
易中天和他女儿 | 来源:易中天微信公众号
参考资料:
1. 《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易中天
2. 《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瑞·达利欧
3.《易中天:中华文明以唐宋为高峰,元明清走了下坡路》,燕京书评
4.《 瑞·达利欧最新演讲:如何利用历史周期应对未来发展》,中信商业家
股票
MORE>-
沪深股票净值
-
05-10跨境电商攻略:小白进阶指南
-
05-10揭秘2024年手机配件市场:Coupang跨境电商新商机!
-
05-10除了低价格,我们还能为客户提供什么价值?
-
05-10成为亚马逊品牌霸主:揭秘获得A+页面权限的关键步骤
-
05-10跨境电商选品攻略:从市场洞察到产品打造的全方位指南
-
05-10发掘网站潜力:SEO内容排名大揭秘!
-
05-10开启新征程:野莓(Wildberries)中国招商,探索俄罗斯市场新机遇!
-
05-10亚马逊专利投诉攻略:5步轻松应对侵权困扰!
-
05-10亚马逊新算法COSMO登场:卖家如何应对?
-
05-10如何挖掘用户真实需求?关键词排名优化攻略揭秘!
-
05-30敢为不凡闪耀全球:TCL连续三届成为美洲杯官方合作伙伴
-
04-23比特币究竟是福是祸
-
04-05探索亚马逊:为何这是你的下一个电商之选?
-
04-05外贸业务员招聘难?别怪外部环境,企业自身也有责任!
-
04-05探索亚马逊:揭秘其强大优势,助你开拓全球市场!
-
04-05深度解析亚马逊买家之声:为何它对你的电商生意至关重要?
- 最近发表
- 标签列表